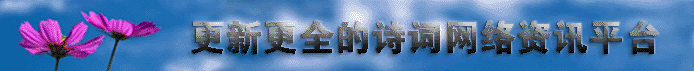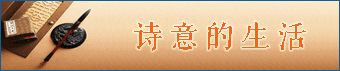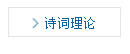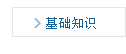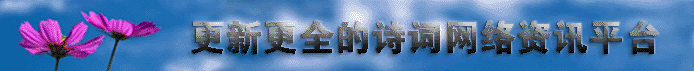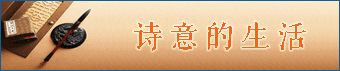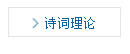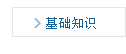词体复活的“标本”
——读《蔡世平词选》
○王兆鹏
一
自从上世纪“新文学”兴起以来,今人写的古体(或称“旧体”)诗词就被排挤在文学殿堂之外了。在现当代文学的户口簿里,古体诗词被注销了户籍;在主流的文学传媒里,基本上见不到古体诗词的踪影;在当今文学理论家、批评家的价值观念中,今人写的古体诗词已不算是文学作品,写古体诗词的人,也不算是诗人、词人了,只有写新诗的才有资格当诗人。作为主流话语的大学教材——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是只讲新诗而不讲古体诗词的。当代人写古体诗词,似乎只能算是业余爱好,摆弄点古色古香的文字游戏而已。
同样是古体诗词,同一种文学样式,古人写的,就被奉为文学的正宗,视若经典,而今人写的,却被摒弃在文学的大门之外,置之不理。今人创作的古体诗词,固然在当今的文坛已不是主流,难与小说散文等文体分庭抗礼,但其作者队伍和作品数量,即使不能跟新诗平分天下,也似乎差距不大。为何古体诗词还只是在文学的屋檐外徘徊呢?元明清三代的诗词,跟唐宋时代的诗词相比已是风光不再,跟同时流行畅销的小说、戏曲的影响力相比也是有所不逮。可历来讲古代文学史,照样不会忽略元明清三代的诗词作品及诗人词家,何以讲现当代文学史,只承认新诗人而不接纳写古体诗词的诗人了呢?
我想,这既是文学观念上的问题,也与古体诗词的创作现状不无关系。当今的古体诗词,要么写得不像,要么写得太像。写得不像,是说名为古体诗词,却不遵守古体诗词的艺术规范,不符合基本的诗词格律,名实不副。任何艺术或娱乐形式,都有自己的规范要求、游戏规则,如同足球比赛,违反规则的进球会判决无效一样,不符合古体诗词形式规范的作品,自然得不到认可。写得太像,是说一味模仿古人,语言是古的,意象是古的,表达方式是古的,连作品的精神气韵也都是古的,分不清是古人写的,还是今人写的。这样的诗词,即使技巧上再高超,艺术上再成熟,也只是一种仿真性的假古董,没有鲜活的个性,没有独特的生命情韵。文学艺术,需要的是鲜活的个性,需要的是独立的生命情韵。
要改变古体诗词这种受冷落的命运,最关键的一点,是古体诗词要能证明自己也能像当今流行的其他文学样式包括新诗一样,能够用今天的语言,表现现实生活、展现时代精神,具有独特的艺术个性,具有不可替代的活力与魅力。
二
最近读到《蔡世平词选》(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6年),不觉眼前一亮,心头一喜:词原来可以这样写,可以借助传统的“有意味的形式”,用当今鲜活的语言,去表现现实生活、展现时代精神,创造出独特的艺术个性,发挥词体特有的活力与魅力。蔡世平的词,不是仿古、复古,而是让古体新生、复活。
关于蔡世平的词,已有不少的评论和争议。如果不是静态地孤立地讨论其词的优劣得失,而是以一种动态的历史的眼光来审视评量,那么,蔡世平的词,应该说为今后词的创作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建立起一种新的审美范式,提供了一个词体复活的成功样本,展现出词体艺术发展的乐观前景。
蔡世平提供的这个词体复活样本的基本特点是:遵古律,用今语,写时事,抒我心。
遵古律,是说蔡世平的词,严格遵守千馀年来凝定的词体艺术的格律规范。古典的词体,是一种具有民族性、本土化的“有意味的形式”,运用它来创作,可以唤起当代读者对传统经典的记忆与回味,对民族形式的亲近与认同。用古典的外型来铸新时代的精神灵魂,旧中有新,新中有旧,既熟悉,又陌生,既新颖,又似曾相识。这样的词作,具有一种情感上容易接近、认同的陌生化的审美效应。所以,读蔡世平的词,既觉得新鲜,又感到亲切,还有几分佩服和敬意。一向被视为难学难作的词,在蔡世平笔下,变得是如此平常又容易、娴熟又自然。他化神秘为平常,变艰难为容易,拉近了古体诗词与当代大众读者的距离,让一般读者和爱好者相信:我们当代人也可以自由轻松地写出这样有兴味的词作。
用今语,是说蔡世平能娴熟自如地用当今生活化的日常语言写词,既通俗易懂,又生动形象,“新鲜活脱”(周笃文先生评语),别具韵味。这是蔡世平词的一大特点,也是他自觉而明确的艺术追求。他在《蔡世平词选·后记》中说:“只有形象化、有特色的语言,才能使词‘原形毕露’,而这种语言又必须是今天的,现代人的。这样的词才能被当代人接受。我比较重视语言的新鲜与张力,表述的随意与自然,尽可能符合现代人的口味。”
语言的生活化、日常性,并不意味着语言的随意性、平庸化而缺乏表现力。蔡世平词的语言,既是生活化的,更是艺术化的,既不失口语的新鲜自然,又工致巧妙。如“昨夜蛙声染草塘,月影又敲窗”(《燕归梁·乡思》),平淡中见奇崛。本写听觉上的蛙声,却用视觉的“染”来烘托;本写视觉上月影的移动,却用具有动作性和声响性的“敲”来表现,反常合道,无理而妙,极富想像力和艺术张力。“敲窗”,从句式上说,应该是“月影”敲窗,但又不妨理解和想像为蛙声随着月影来“敲窗”,一如稼轩词的“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说“丰年”的不是作者,不是老农,而是蛙声。所以这“敲窗”的,既可以是月影,也可以是“蛙声”。两句动静结合,声、光、色、态俱全,意境浑成,如交响乐,似有声画。有些语言,虽然明白如话,却生动传神。如《浣溪沙·初见》:“叫句老师唇没动,改呼宝贝口难张。慌忙粉面映羞郎。”写两位特殊身份的恋人初次见面表达情愫时的羞涩,就非常传神。少女欲喊原是老师辈的恋人为“老师”,觉得有点不亲切,担心产生隔阂;又想径直改口称呼为“宝贝”,又羞于启齿,害怕误解为轻狂。于是,女越慌张,郎更羞涩,女子的“慌忙粉面”映射着羞涩的郎君,目光交织,又时而回避,低面垂眼,又时而对视。此时的情意缠绵悱恻,无声胜有声。这叙述初见的句子,与北宋柳永描写分离的名句“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有异曲同工之妙。
柳永的词,走的就是民间化、通俗化的路子,用人们易于理解和接受的生活化的语言来歌唱大众感兴趣的时事和情感,所以他的词,在当时广受民众欢迎,以致“凡有井水饮处皆可歌柳词”。特别是不知书识字人更加亲睐喜爱,所谓“不知书者尤好之”。柳永的词,一度改变了词体发展的方向,即由追求贵族化的审美趣味转向迎合适应平民化的审美追求。自然,我们现在不能说,蔡世平堪比宋代的柳永,但就今后词体的发展进程而言,我想,蔡世平的词,也许会具有柳永词类似的作用和影响,至少能给人一种启示,古典的词体,是可以走当代化、民间化、大众化的道路的。
写时事,是说蔡世平的词富有时代感和现实感。他的词,既不是模仿古人,没事说事,也不是吟风弄月,显摆点“小资”情调,更不是诗朋酒友之间的无聊应酬,附弄点风雅,而是以一种严肃而虔诚的创作态度,用词体来表现时代生活,展现当代人的生存状态。虽然这类词作的数量,在《蔡世平词选》中所占比重不大,但还是引人注目的。比如C城湘风茶楼收养的一个私生女孩,年渐长而不知其父,词人特为之作《贺新郎·寻父辞》,“求其父爱慰藉,也唤醒天下人父之心”;“天平应在天心处。又为何,阳光只进,那边门户。总举呆头伸泪眼,多少邻童笑语。真羡慕,娇儿宠父。都说茅根连地腑,是俺爸,应感儿的哭。心缺了,谁来补。”这声声“嘶裂凄凉句”,既展现出都市华灯暗影里弱者的另一种生存状态,又坦露出词人的一片诚挚的爱心。又如《蝶恋花·路遇》写一乡下汉子的不幸遭遇,两个儿子患白血病,其妻畏贫,弃家而去,词人既感慨世间道德的沦丧,吁请正义良知的回归:“世道仍须心养护。岂料豺狼,叼向茅丛处。”又为病儿深掬一把同情之泪:“谁说病儿无一物,还留血泪和烟煮。”这词作,让我们想起了汉乐府《妇病行》中那临终而念念不忘饥寒儿女的善良病妇。古今对照,深感人心不古。而这样关注社会底层弱者命运的词章,在唐宋词里是找不到的。
蔡世平的词,也有写欢乐、美好生活场景的。如《青玉案·兵婚》写新疆军营里的婚礼,洋溢着热闹与喜庆的气氛;《念奴娇·故乡行》写1979年从兵营回乡探亲时所见政治环境的变化给家乡乃至整个国家带来的新气象,不落俗套。结句“沧桑如许,湘江又透新月”,既有对“浩劫年年,河山泪滴,遍体鳞伤血”往事的感伤,又有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寓深沉的感慨于“新月”的意象之中,耐人寻味。
2003年肆虐神州的那场“非典”,是当年整个世界都关注的大事,人们至今记忆犹新。作者也以纪实性的笔调,写了一首《贺新郎·非典》,感念生命之无常,表现“闹市而今少人行,更有白纱遮面。车船上,喧声不见”的恐怖场面,同时也表达了战胜非典的信心:“镇妖我有昆仑剑。战云飞,铺张巨网,捉他遍遍。血铸长城铜铁志,哪给魔魂方便。似看见,雾消云散。”这信心,来源于民心的空前团结,来源于政府得力的抗击举措。所以,作者这种必胜的信念正表现出乐观自信的时代精神。
抒我心,是说蔡世平的词,注重抒写自我独特的人生体验,表现自己的真实性情,具有独特的生命个性。宋代苏东坡、辛弃疾词的不朽魅力,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在词中展现了词人独特的精神风貌、情感世界、人格个性、人生态度。金代著名诗人元好问就说过东坡词“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遗山先生文集》卷三六《新轩乐府引》)。蔡世平的词,也表现了他的情感个性、他的生命体验。他深知“艺术的本质在于逼近人的精神世界”,“内在的精神质地才是词的生命”(《蔡世平词选·后记》)。他的词,不是有意做出来的,而是有感而发,从心田里自然流淌出来的。他在谈创作体会时说:“词的高妙之处,是表现人的微妙的灵动的情感。因此,真正意义上的词,是在词人心里养着的。一句不经意的话或者一件微不足道的事,触动了词人,词随心动,心与词飞。于是,词句就自然而然地吐了出来”(同前)。这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词人的经验之谈、甘苦之言。清末四大词人之一的况周颐也说过:“吾听风雨,吾览江山,常觉风雨江山外有万不得已者在。此万不得已者,即词心也。而能以吾言写吾心,即吾词也。此万不得已者,由吾心酝酿而出,即吾词之真也,非可强为,亦无庸强求。视吾心之酝酿何如耳。吾心为主。吾心为主,而书卷其辅也。书卷多,吾言尤易出耳”(《蕙风词话》卷一)。蔡世平所说的“词在心里养着”与况氏所言“词心”、“吾心酝酿”,可谓一脉相承。词从心里流出,才是真情,才有个性。
蔡世平生长于农村,而工作在城市,居住在城市,但热爱自然、向往乡村宁静的本性不改,他在词中宣称:“乡里汉,城中久住,亲昵还是泥巴。”(《汉宫春·南园》)。这种热爱自然、热爱乡村的本性,使他的词充满泥土的芳香、乡村的气息。如“且将汗水湿泥巴,岁月便开花”(《朝中措·地娘吐气》);“短梦耕泥夜夜勤,晴播莺声,雨播虫声。眸田总种一园春,行也茵茵,坐也茵茵”(《一剪梅·短梦耕泥》);“总记得,花猪栏里闹;总记得,花鸡枝上叫。荷花白,谷花黄。归来放学抓猪草,几家玩伴捉迷藏”(《最高楼·悲嫁女》)。作者善于将平常的语言变得不平凡,将平凡的乡村生活变得有诗意。人类原本要诗意地栖居。而这“诗意”,原不在物外,不在居住环境条件是否有诗意,而在人的内心有无诗意,能否在平凡的生活中、平常的景物中发现诗意,发现美感。蔡世平能在平常的乡村景物中发现诗意,更能创造出诗意。这是他的特长,是他创作的奥秘所在。而这种诗意地对待生活,对待自然,从思想渊源上说,应该来自于宋代的智慧老人苏东坡,东坡在《前赤壁赋》里说:“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这种审美态度,不仅是对创作,对人生处世又何尝没有启示?
蔡世平曾经是军人,有过十多年的军旅生涯,因此,他的词有着军人的豪情、男子汉的血气。请看其《贺新郎·说剑》:“石光铁火铜风起。便造了,河山筋骨,男儿血气。从此文心悬剑胆,山也横成铁笛。”另一首《贺新郎·致陈泥》,对徒步行走长江的四十岁汉子表示钦敬。虽“野风悍,撕残衣袖”,但陈泥决心不改“男儿四十雄心久。最输他,温柔乡里,消磨时候。捉住长江头更尾,赢得精神不朽。”这“铁步裁山还剪水”,是何等气概!这意象,这气势,在唐宋词也难得找见!
军人也有柔情,也常想念心中的那个她,也有相思,也有苦闷:“殷勤问我楼兰客:咫尺总天涯?夜来只待,塞风放梦,湘水翻花”(《秋波媚·望城思绪》);“寸寸相思涉水来,枕上波澜冷”(《卜算子·静夜思》)。但跟古人不同,军人出身的蔡世平,不是一味的苦闷抑郁,总能在苦闷忧患中振起超脱,充满着乐观的精神:“闲来整理相思调。幸有只,填词手,做个坟堆,葬他烦恼”(《霜叶飞·剑断沙场》);“唤得南疆千犬吠,洗我柔肠”(《浪淘沙·月影浮霜》)。即使是写柔情,也写得大气磅礴,境界高远。
遵古律,用今语,写时事,抒我心,这四点,各自分开孤立地看,都不足为奇,说不上是优点特长。词中遵守格律,是基本要求,何足为优点?用日常性的生活语言,似乎也不是难事,但用今语而严守古律,则非易事。用合乎格律的鲜活语言来表现时事,表现自己的人格个性,生命体验,就更罕见。如同高个子巨人不稀奇,篮球技术高超的人也常见,移动快速和反应灵敏的人更多如牛毛,但这三点集中在姚明一个人身上,就造就了他在NBA赛场上独特的这一个,构成了作为篮球明星的特质。同样的,遵古律,用今语,写时事,抒我心,四者的有机融合,就构成了蔡世平词独特的艺术个性和审美魅力。
这种个性和魅力,又成就了蔡世平作为词人的条件。在我看来,蔡世平已有资格称为词人,也应该称为词人。蔡世平的词,比时下有的官方评定认可的所谓“一级诗人”写的新诗,要有价值和韵味得多。蔡世平写词是认真的,他是把写词当一种事业来追求,他有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想振兴词,写好词。对此,他曾著文在理论上呼吁,在词的创作实践中也时有表露:“近来词客好心焦。长短句,句句不妖娆”(《小重山·春愁》);“梦写情词,醒来尴尬平常句。夜深明月影双双,和泪相思诉。无奈肚空笔瘦”(《烛影摇红·八景文思》)。
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一的杨万里曾有诗说:“不留三句五句诗,安得千人万人爱”(《诚斋集》卷十《醉吟》)。作为词人的蔡世平目前至少给我们留下了“三句五句”好词,必将赢得千人万人爱。除前举一些好词好句之外,下面这些词句也都很有特色:
又渔歌摇得,月眠湖睡。(《满江红·青山血祭》)
才送洞庭星,又赶昆仑月。(《生查子·月满戍楼》)
古意千年,泪也捂成酒。声声苦。醉肠醉腑,一夜河山瘦。(《点绛唇·南疆犬吠》)
天上星高几个,水中几个星低。麻蛙几个拥荷衣。声声衔月色,夜夜惹乡思。(《临江仙·荷塘》)
土屋柴炊锅煮泪,真味,民间烟火最熏心。(《定风波·落卷坡居住记》)
三
蔡世平虽然已到知天命之年,但词的创作历程还比较短暂,从他2002年尝试写词算起,至今也不过三、四年的时间。可以说,在词的创作方面,他还是个“新手”。刚刚入行试手,就出手不凡,写出了许多具有相当艺术水准的成功词作,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今后的创作道路上,蔡世平的词会越来越成熟完美。我们也期待他这颗词坛上的“新星”能逐步变为“明星”,进而成为“巨星”,创作出更多浑然天成、能感发人心的优秀词章,把词引领到一个新的艺术天地,推进到更高的艺术境界,提升词在当代文化生活、文学领域中的影响力和认同度,最终把词从当代文学的边缘角落引领入文学的中心地带,使古体的词跟新诗一样成为当代文坛上一道亮丽的风景。到那时,就像当年南宋一样,词可以堂堂正正地与诗并称,人们说起“诗词”,就不仅仅是指古代的古典诗词,也指当下的新诗旧(体)词。
蔡世平的词创作,正处在“现在进行时态”,而不是“完成时态”,在今后行进探索的途中,还有不少需要完善的地方。如形式上的用韵过宽,时有落韵、出韵之病,《贺新郎·从军别》和《贺新郎·叶落秋心》用“树、肚、走、熟、袖/宿、锈、诉、透、吐、候、烛”等字押韵,就出韵而不协调。不管是用古韵还是用今韵,一个基本原则是,同一首作品押韵的韵字,应该是同一韵部的字,即韵母相同的字。这其中可能有使用方言读音的原因,但词毕竟是写给南北读者共同阅读的,所以今后用韵要更严格一些。
词中的题序也还可以再斟酌。作者是很在意题序的写作的,但有些词的题目过于虚泛模糊,不便于读者准确了解把握词中的情感指向、情感内涵。诗题词题,不同于文本中的语言,应该尽可能明确具体。词中题序的功能,主要是让读者了解写作的时、地、事、因,而不要让读者去猜谜。也许作者认为词题的诗意化、虚泛化、多义性可以增加词的艺术张力,我却以为,发挥强化诗词艺术张力作用的,应该是诗词文本的语言,而不是题目。
词序中的语言风格应该统一,一篇之中,要么用大白话,要么用言简意赅的文言。有的词序是大白话与文言语辞夹杂,读起来也不太和谐。如《卜算子·静夜思》词序:“一九七五年一月戍边新疆。新兵连戍卒睡地铺。零下二十多度,滴水成冰”,“后来戴了皮帽子睡觉”。以日常白话为主,其中的“戍卒”就不符合今天的习惯称谓,不如直接称“战士”。
至于“内在的精神质地”,则需要更广泛地拓展题材,表现更为丰富的时代风情和人生世相,抒写更深刻的生命体验和人生况味。杨海明教授写的《唐宋词与人生》(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2年)是一本值得参考的理论著作。
衷心希望词人蔡世平能在以后的创作道路上,有进一步的创获。也希望,能有更多的诗词爱好者,能够在《蔡世平词选》这一当代词体复活“标本”的启示和引导下,为我们的时代,抒写出更多优秀的词章。
(王兆鹏: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词学研究会会长,武汉大学中国文学传播与接受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中国韵文学会副会长,中国宋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文学遗产》编委,《宋代文学研究年鉴》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