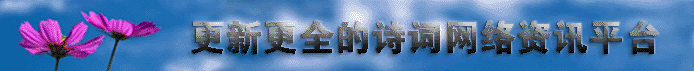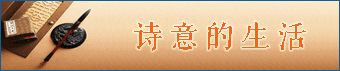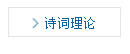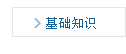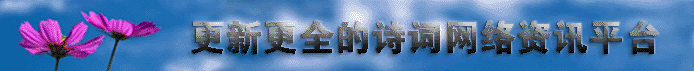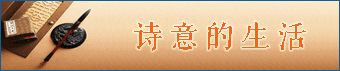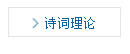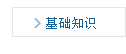|
陈寅恪先生1958年春曾写有《南海世丈百岁生日献词》七律一首,尾联云:“玉谿满贮伤春泪,未肯明流且暗吞。”余英时1982年即已拈出此句,谓:“对陈寅恪先生晚年心境的刻划再也找不到比这两句诗更恰当的了,”此说极为有见。但余文以为这两句诗仅仅表示陈氏“失去了公开痛哭的自由” ,则似尚有未达之一间。胡文辉认为“玉谿满贮伤春泪”一句“似泛指李商隐诗的伤感风格,借以自比。‘伤春’可能特指李商隐《曲江》:‘天荒地变心虽折,若比伤春意未多’。” 胡氏指出“伤春”古典的这一可能,极为重要。初看起来,陈氏此联所谓“伤春”确有泛指和特指的两种可能。如为泛指,则是“伤时例托伤春惯”之义, 古代诗人例借“伤春”以寓“伤时”之慨,陈氏借以自比,实则是说“义宁满贮伤时泪,未肯明流且暗吞”。若如胡氏以为泛指李诗的伤感风格,则并不准确。如为特指李商隐《曲江》一诗,则其中极可能隐藏了陈氏本人对作为古典的《曲江》一诗的独特理解,他将古今融会,合并致慨。陈氏以为:“古事今情,虽不同物,若于异中求同,同中见异,融会异同,混合古今,别造一同异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觉,斯实文章之绝诣,而作者之能事也” 。所以如为特指,则“伤春”一联就正是所谓“同异俱冥,今古合流”的典范。那么,陈寅恪诗中的所谓“伤春”,当同李商隐诗中的“伤春”一样,必然都应是较之“天荒地变”更为深刻的一种悲哀。如果“伤春”古典的这一特指可能成立,则对于我们理解陈先生的晚年心境至关重要。而无论其为泛指或特指,陈氏此联的重点,实在乃是“未肯明流且暗吞”一句。“伤春”之泪所以会有“明流”或“暗吞”的分别,正是代表了诗人特殊的时代处境。余英时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认为此联极为恰当地刻画了陈氏的晚年心境。但余氏尚未注意“未肯”二字,陈诗对“伤春”之泪作“明流”、“暗吞”的分别,复再加以“未肯”的表示,此种坚定决绝的口吻,其中所深隐的乃是陈氏最为幽微曲折的晚年心境。从这一点来看,如果“伤春”为泛指,则“玉谿满贮伤春泪”一句只不过借李商隐自比,至于“未肯明流且暗吞”则仅谓一己之感,并不与李氏发生联系。“伤春”本为文学史上常见的主题,历代诗人伤春之作不知凡几,其中以“伤春”寓写“伤时”之慨的作品亦复难以数计,所以钱钟书才说“伤时例托伤春惯”,然而陈氏何以独举“玉谿伤春”为比?而且无论从七律尾联上下句承接继起的结构来看,还是从句义本身来看,“玉谿满贮伤春泪”与“未肯明流且暗吞”都不当截然断裂,以上句兼以拟人,下句独然谓己。因此,泛指之说实甚难成立。本文即欲论证陈诗所谓“伤春”决为特指李商隐《曲江》一诗而言,且藉此分析陈氏在玉谿“伤春”之泪的古典之中所寄寓的个人身世与时代盛衰方面的奇哀深慨。
一、古典中的玉谿“伤春”考实
兹先将此二首“伤春”之作抄录于下:
南海世丈百岁生日献词
又题《今年戊戌旧历二月初五日为康南海先生百岁生日其女罗夫人同璧设祭京寓远道闻之感赋一律不必投寄也》
此日欣能献一尊,百年世局不须论。看天北斗惊新象,记梦东京惜旧痕。
元祐党家犹有种指新会某世交也,平泉树石已无根借用李文饶《平泉山居戒子孙记》中“非吾子孙”之意。
玉谿满贮伤春泪,未肯明流且暗吞。
(按:《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弁言》及吴宓钞存稿中第六句皆作“江潭骚客已无魂”,且颈联无自注)
曲 江
望断平时翠辇过,空闻子夜鬼悲歌。金舆不返倾城色,玉殿犹分下苑波。死忆华亭闻唳鹤,老忧王室泣铜驼。天荒地变心虽折,若比伤春意未多。
陈寅恪力倡“古典”、“今典”之说,以为“诗若不是有两个意思,便不是好诗” ,亦即钱谦益所说的“诗文一道,故事中须再加故事,意思中须再加意思” ,且陈氏无论作诗、论诗,皆讲求“语语相关,字字有著” ,这造成了寒柳堂诗每苦意深,而在文本方面则缺少直接感发力量的特色,但我们却也只能以此思路来解读他的诗歌。
(一)“伤春”:时代盛衰中的女性悲剧命运
陈寅恪对于李商隐《曲江》一诗所谓“伤春”自有其理解与共鸣,除去“玉谿满贮伤春泪,未肯明流且暗吞”一联以外,寒柳堂诗中还有两处明确提到《曲江》:一处是1964年所作《题〈小忽雷传奇〉旧刊本》绝句四首其二:
赞皇白傅史称贤,甘露沉冤论颇偏。惟有义山超党见,伤春诗句最堪传。
另一处是1965年《乙巳冬日读〈清史后妃传〉有感于珍妃事为赋一律》诗中自注:
昔日曾传班氏贤,如今沧海已桑田。
伤心太液波翻句玉谿生诗悼文宗杨贤妃云:“金舆不返倾城色,
玉殿犹分下苑波。”云起轩词“闻说太液波翻”即用李句 ,回首甘陵党锢年。
家国旧情迷纸上,兴亡遗恨照灯前。开元鹤发凋零尽,谁补西京外戚篇。
前一首胡文辉《笺释》已指出,所谓“伤春诗句”即指《曲江》末句,甚是。李商隐诗涉“甘露之变”而有“伤春”二字的仅有“天荒地变心虽折,若比伤春意未多”一联。陈诗意谓李商隐超越了赞皇(李德裕)、白傅(白居易)挟“私嫌”、“党见”而对甘露之变做出的偏颇评价,其“伤春诗句”才是陈氏最为欣赏,最堪传述的“诗史” 。后一首中的自注则更明确地表示陈氏以为《曲江》一诗乃是为“悼文宗杨贤妃”而作。结合以上两种认识,我们可以判定陈氏对《曲江》一诗的理解基本信从冯浩的说法 ,因为《曲江》一诗解者甚众,异说纷纭,而以《曲江》为伤悼杨贤妃且兼甘露之变而言者,仅冯氏一家。《玉谿生诗集笺注》解《曲江》一诗云:
凡诗须玩其用意用笔,正陪轻重,乃可引事证之。今次联正面重笔,即所谓伤春,五六 乃陪笔耳。此盖伤文宗崩后,杨贤妃赐死而作也。杨贤妃有宠于文宗,晚稍多疾,阴请以安王为嗣,密为自安地。帝谋于宰相李珏,珏非之,乃立陈王成美。妃与宰相杨嗣复宗家,及仇士良立武宗,遂摘此事,谮而杀之。诗首句谓文宗,次句谓贤妃,三四承上,五六则以甘露之变作衬,而谓伤春之痛较甚于此。盖文宗受制阉奴,南司涂炭,已不胜“天荒地变”之恨,孰知宫车晚出,并不保深宫一爱姬哉!语极沉郁顿挫。……余深味此章与下章(按:指《景阳井》)杨贤妃之死也,必弃骨水中,故以王涯辈弃骨渭水为衬,实可补史之阙文,非臆度也。四句似亦以弃骨水中,故云分波。
观乎《乙巳冬日》诗注,可知陈氏于《曲江》次联印象极深,或即依冯氏之说,以“金舆不返倾城色,玉殿犹分下苑波”为“伤春”,即以“伤春”为伤于“不保深宫一爱姬哉”。意者当陈氏读到冯浩据“分波”二字所臆造的杨贤妃“弃骨水中”之说时,想必一拍即合,故留有极深之印象。因为冯浩此种表微发覆的解诗之法,正是陈氏本人所欣赏和实践的方法,而且冯浩以为其“分波”之说,“实可补史之阙文”,此点亦极符合陈氏“以诗证史”、“以诗补史”的理想 。而更有可注意者,前引两首陈氏提到《曲江》“伤春”的诗作,乃都是以叙写女性在世乱之中悲剧命运的故事或史实为触发的:《小忽雷传奇》据唐代段安节《乐府杂录》中的故事改编,主角郑盈盈(即郑中丞,中丞为宫人之官)被虚构成甘露之变主谋之一的郑注之妹,以小忽雷(琵琶)为线索,并杂入白居易《琵琶行》的故事,《乐府杂录》中还有郑中丞“以误圣旨命,内官缢杀,投于渭河”的情节 ;至于珍妃被慈禧投于井中,则更是晚清世变之中女性命运的又一幕悲剧。陈氏之所以对这一主题有如此不衰的兴趣 ,和他晚年“著书唯剩颂红妆”的心境极有关联。他写作前引二诗时,《柳如是别传》已经完成,后者当然更是其所谓“颂红妆”的绝大著作,而1964年《别传》的《稿竟说偈》(初稿本所附)中竟也有“刻意伤春,贮泪盈把”一语,胡文辉以为“刻意伤春”即用李商隐《杜司勋》一诗中“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惟有杜司勋”之句 ,这从字面来看是不错的。然而胡氏也注意到“贮泪”与“玉谿满贮伤春泪”用语相同,其实“刻意伤春,贮泪盈把”正与“玉谿满贮伤春泪,未肯明流且暗吞”极为接近,余英时即牵合二者为说 。如果从前面分析的陈氏以“伤春”为悲悼女性在时代盛衰迁变中的悲剧命运来看的话,《稿竟说偈》的所谓“伤春”,对于河东君而言,也是极为恰当的。而所谓“刻意”云者,或许正是《别传》之“别”的寓意所在,陈氏正是要借“伤春”和女性来寄寓其古今盛衰的无限悲慨。吴宓1961年与陈氏谈话后有日记云:“寅恪之研究‘红妆’之身世与著作,盖藉此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意存焉,绝非消闲、风流之行事……。” 故在陈氏心中,李商隐的“伤春”之泪,也正是寄寓了他的“伤时”之慨。
(二)“伤时”:女性悲剧命运中的时代盛衰
关于“伤春”例寓“伤时”之慨,且常常融入作者个人身世之感,《柳如是别传》中陈氏分析钱谦益“踏青无限伤心事,併入南朝落照中”一句时曾说:“更疑牧斋在弘光元年(按:1645)上巳时节,曾预赐宴之列,今存是年之官书,阙载此事。或又曾偕河东君并马阮辈作踏青之游,因《有学集》关于此时期之作品,皆已删除,故亦无从考见。果尔,则此首乃述其个人之具体事实,而非泛泛伤春之感也。” 可见他不仅认同“伤时例托伤春惯”之说,而且还以为“伤春”之中常常隐寓了“个人之具体事实”。
“天荒地变心虽折,若比伤春意未多”,从文本上即可看出“伤春”之外更有事在,必具深旨,“非泛泛伤春之感也”。因为李商隐在“伤春”之上,还加入了一层限定和形容,即其所慨叹之“伤春”,乃是比“天荒地变”更为深刻的一种悲哀,此所谓“意未多”。那么李诗中的“伤春”,究竟是何等的一种奇哀深慨呢?陈寅恪体会到李诗“伤春”必有深旨,他推寻的结果,认为那是“伤文宗崩后,杨贤妃赐死”之义,然而问题尚不止此。
陈氏既以“伤春”为悲悼女性在时代盛衰迁变中的悲剧命运,则自亦可以从女性之悲剧命运中看到时代之盛衰。笔者初疑陈氏何以有“惟有义山超党见,伤春诗句最堪传”之论,以杨贤妃之始则邀宠自安,终于遭谗贾祸而言,何以伤悼杨氏,其诗就成为最堪传述的“诗史”了呢?其实陈氏心中,李商隐《曲江》虽为悼杨贤妃而作,而其所致慨者,绝不仅在贤妃之赐死。陈氏既从冯浩之说,必定也注意到冯氏“盖文宗受制阉奴,南司涂炭,已不胜‘天荒地变’之恨”一语。陈氏本人于唐史素有专攻,他对甘露事变前后之时代政局本有极深之认识,如其《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即曾言:
通鉴纪二四五太和九年十一月壬戌即二十一日甘露事变,其结论有云:“自是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诚道其实也。……自此以后,唐代皇位之继承完全决于宦官之手,而外朝宰相惟有服从……
后文引两唐书、《资治通鉴》等史料以证文宗、武宗两朝之事,亦曾引及关于杨贤妃之记载,陈氏案语云:
上引文宗、武宗两朝间史料,亦皆唐代皇位继承不固定及一时期宫掖阉寺党派竞争决定后,李氏子孙充傀儡,供牺牲,而士大夫党派作阉寺党派之附属品,随其胜败以为进退之明显例证也。
后文陈氏还说:
唐代内廷阉寺决定帝位继承之经过及李氏子孙作傀儡牺牲之悲剧,史乘殊多阙漏,要为与前此相似,乃一种公式化之行动,其概况亦可推知也。
陈氏既以《曲江》“伤春”为必具深旨,且其“伤春”之慨较“天荒地变”为尤甚,则必不以玉谿“伤春”为仅悼杨贤妃之赐死,从可知矣。冯浩《笺注》正兼甘露之变而言,因此陈氏盖即以为李商隐以伤杨贤妃寓写伤时之慨,其所慨者乃为冯笺所谓“受制阉奴”,亦即陈著所谓“李氏子孙作傀儡牺牲之悲剧”,而这乃是比甘露之变屠戮朝臣的“天荒地变”更为深刻的一种悲剧 。至于“伤春”中有关李商隐的“个人之具体事实”,亦有可得而言者。文宗“受制阉奴”之情形,李氏当有极深之认识。盖太和九年李氏方往来京、郑,应举不第,然于是年年终,亦已有《为郑州天水公言甘露事表》一文 ,且更由于令狐楚之关系,李氏或于宫中隐秘,得所预闻。《旧唐书·令狐楚传》载:“(李)训乱之夜,文宗召右仆射郑覃与楚宿于禁中,商量制敕,上皆欲用为宰相。楚以王涯、贾餗冤死,叙其罪状浮泛,仇士良等不悦,故辅弼之命移于李石。”后二年(开成二年)令狐楚卒,其卒前一日曾嘱李商隐代草遗表,仍殷殷以“殁者昭洗以云雷”为念, 所以李氏《奠相国令狐公文》乃有“临绝丁宁,讬尔而存” 之语。文宗之崩与贤妃之死在开成五年,令狐已不及见,李氏发为“天荒地变心虽折,若比伤春意未多”之叹,于时局乃是有极深之悲慨的。
有了以上关于陈寅恪对于“伤春”的认识,我们才能正式讨论《南海世丈百岁生日献词》一诗中所深隐的陈寅恪晚年心境及其与玉谿“伤春”之泪的关系。
二、今典中的玉谿“伤春”表微
《南海世丈百岁生日献词》一诗,若从颈联的自注来看,谓指有感于梁思成改易其父志之事,乃是可以肯定的 。然而陈氏全诗决为一篇俯仰百年(谓康有为),神接千古(谓李商隐),寄寓个人身世与时代盛衰之奇哀深慨的作品,其重点并不在以自注明白述说的颈联,乃在其“同异俱冥,今古合流”,明以拟人,实则谓己的末联。
1965年陈氏将此诗收入《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之《弁言》中,谓:“昔年康更生先生(有为)百岁纪念,因感吾家与戊戌政变事,曾为赋一律”云云 。1958年不仅为康有为百岁冥诞,亦为戊戌变法六十周年,因此陈诗首联即表示其所致慨者,乃为“百年世局”,而非域于一人一事,一地一时。颔联“看天北斗惊新象,记梦东京惜旧痕”,胡文辉《笺释》谓“新象”比喻“新社会”,陆有富君谓疑指戊戌变法中时局之“新象”。笔者以为两说或可并存,依胡氏之说,则以“新社会”(1958)与戊戌时局(1898)对比为言;依陆君之说,则以戊戌一年事集中致慨,谓虽惊喜于维新变法“新象”之新,而何悲惜于南柯短梦梦破之速也。《笺释》谓“记梦东京”化用《东京梦华录》书名,因其后有“元祐党家”一语,此说自极为可能。而如果依陆君之理解,则以“惊”喜、悲“惜”对举,“记梦东京”或可谓康梁逃难日本,梁氏之撰写《戊戌政变记》等事,此则皆在戊戌一年之内,故为感叹维新之梦何其如此短且速也。此联重点在下句“记梦东京”一语,不论取何者之说,当同为致慨于维新事败之义,故二说可以并存,于全诗并无影响。陈氏以其祖父、父亲在清末积极参与新政之故,于维新事败尚别有个人家世及身世之感,所谓“记梦东京惜旧痕”,与一般泛泛伤时、咏史之作自有绝大之不同。颈联因有自注,意极明确,胡氏笺释已甚精详,可以参看。其重点在下句自注引李德裕《平泉山居戒子孙记》中“非吾子孙”一语,以此谓指梁思成改易其父志,自无可疑。《笺释》所引梁思成1957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陈氏自有可能寓“耳”。《笺释》更谓陈氏对此“可能特别反感,故讥刺颇为严厉,而兼有痛惜之感。”胡氏所言甚是。
两首“伤春”七律的重点,都在最后一联。“玉谿满贮伤春泪,未肯明流且暗吞”,例同李诗,陈氏也在“伤春”之上加入了一层限定和形容,即其所满贮之“伤春”之泪,乃是独自暗吞而未肯明流的。陈氏对《曲江》“伤春”之慨的认识既已有如上述,那么他以李商隐自比,在“古典”之中所寄寓的“今典”的悲慨,至此才能豁然贯通,那正是对类似于“受制阉奴”,“充傀儡,供牺牲”那样悲剧的深慨奇哀。果尔,则义宁“此篇所见,殊为深远,似已预知后来之事者。” 然而关于“伤春”二联的“同异俱冥,今古合流”,则犹有待发之覆。
(一)释“受制阉奴”:“伤春”诗句中的史家之识
首先,陈李所哀者皆为“受制”于人之悲剧,不过其所哀之对象,一为“元祐党家”之子孙,一为李唐皇室之子孙而已。陈寅恪之以梁思成改易其父志为“受制”违心者,当出于他对时局的认识。所以陈诗颈联若依胡文辉《笺释》之说,则“痛惜”之感尤多于“讥刺”之意。且颈联下句“平泉树石已无根”的讥人之语,在陈氏最后撰定的《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中,已改作“江潭骚客已无魂”的自况之辞了,此则最可窥见陈氏的本意。
至所谓“阉奴”,则陈氏取譬之不苟,更有可得而言者。盖于陈氏史家之观念中,“阉寺阶级”与“士人阶级”在文化与政治上常处于对立之地位,《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分析统治集团中之两种阶级即曾谓:
一为受高深文化之汉族,且多为武则天专政以后所提拔之新兴阶级,所谓外廷之士大夫,大抵以文词科举进身者也;一为受汉化不深之蛮夷,或蛮夷化之汉人,故其人多出自边荒区域。凡自玄宗朝迄唐亡,一百五十年间身居内廷,实握政治及禁军之权者皆属此族,即阉寺之特殊阶级是也。
《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一文亦曾谓:
唐代自中叶以后,凡值新故君主替嬗之际,宫禁之中,几例有剧变,而阉宦实为此剧变之主动者。外廷之士大夫,则是宫禁之中阉宦党派斗争时及决胜后可怜之附属物与牺牲品耳!
此外,陈氏1953年9月所撰《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一文尤可注意。他在论释曹孟德“求才三令”实为转移世运之绝大变革时,特别强调了其出身阉寺的阶级背景,陈文略云:
东汉中晚之世,其统治阶级可分为两类人群。一为内廷之阉宦。一为外廷之士大夫。阉 宦之出身大抵为非儒家之寒族,……主要之士大夫,其出身则大抵为地方豪族,或间以小族,然绝大多数则为儒家之信徒也。……夫曹孟德者,旷世之枭杰也。其在汉末,欲取刘氏之皇位而代之,则必先摧破其劲敌士大夫阶级精神上之堡垒,即汉代传统之儒家思想,然后可以成功。读史者于曹孟德之使诈使贪,唯议其私人之过失,而不知此实有转移数百年世局之作用,非仅一时一事之关系也。……孟德三令,大旨以为有德者未必有才,有才者或负不仁不孝贪诈之污名,则是明白宣示士大夫自来所遵奉之金科玉律,已完全破产也。由此推之,则东汉士大夫儒家体用一致及周孔道德之堡垒无从坚守,而其所以安身立命者,亦全失其根据矣。故孟德三令,非仅一时求才之旨意,实标明其政策所在,而为一政治社会道德思想上之大变革。顾亭林论此,虽极骇叹(日知录一三正始条 ),然尚未尽孟德当时之隐秘。盖孟德出身阉宦家庭,而阉宦之人,在儒家经典教义中不能取有政治上之地位。若不对此不两立之教义,摧陷廓清之,则本身无以立足,更无从与士大夫阶级之袁氏等相竞争也。
借用陈氏文末一语,可谓“论古今世变者,读书至此,亦未尝不为之太息也。”根据其以上的史家之识,我们才能体会陈氏“伤春”一联的“推理之明”与“料事之确”。
(二)释“天荒地变”:陈寅恪的“元祐党家”情结
复次则有隐含的“天荒地变”一语。陈李所谓“伤春”都是比“天荒地变”更为深刻的一种悲哀。李氏诗中之“天荒地变”乃谓甘露之变,南司涂炭而言,而“伤春”之痛较甚于此。陈氏心中之“天荒地变”则指戊戌政变,维新事败无疑。然则此陈氏心中之“天荒地变”较其“伤春”之慨,“意”亦有所“未多”者,果何说耶?盖于陈李二氏心中,“李唐皇室”与“元祐党家”皆为一时盛衰兴亡之所系,而其子孙竟沦落至“受制阉奴”,“充傀儡,供牺牲”之命运者,实为时代莫大之悲剧。且李氏所哀者,不过一家一姓而已,至陈氏之所哀,则有“士之群体自觉”与“个体自觉” 今已荡然无存之意,其中尚隐寓有陈氏“个人之具体事实”,更有可得而言者。
所谓“元祐党家”,为陈氏屡借以自道家世之语,原出《渭南文集》。陆游祖父陆佃本为王安石之门人,因持论平正,又为新党所不喜,名列元祐党籍。蔡京拜相后,窥徽宗意旨所在,立“元祐奸党碑”,大肆迫害异己及其子弟。时陆佃已故,亦列名其中。陆集表、启中屡有“偶以元祐之党家,获与绍兴之朝士”、“哀元祐之党家,今其馀几,数绍兴之朝士,久已无多”、“伏念某元祐党家,绍兴朝士”等语。 陈氏1927年已有“元祐党家惭陆子”(《王观堂先生挽词》)一语,因其祖父、父亲力与维新,支持变法,终坐以“滥保匪人”、“招引奸邪”之罪名而遭革职,“永不叙用”,所以他以陆游自比。其所谓“惭”者,即自愧没有绍述家风,不如陆游之以“元祐党家”而与于“绍兴朝士”之列。1945年《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文末,陈氏又用此典,谓:“此时悲往事,思来者,其忧伤苦痛,不仅如陆务观所云,以元祐党家话贞元朝士之感已也。” 至于1958年“元祐党家犹有种”一句,虽然注云“指新会某世交也”,但笔者颇疑此注为蒋天枢闻之于师所补记,而不似直出陈氏之口吻者,乃就其要点指示诗意,并非欲读者死于句下笺也。方其吟写之际,则陈寅恪、康同璧、梁思成,是皆“元祐党家”之“种”,且从《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中陈氏最后改定的“元祐党家犹有种,江潭骚客已无魂”(无自注)来看,其自叹身世之意,岂不更为明显? 那么,他为什么对自己“元祐党家”的身世如此念兹在兹,未尝或忘呢?
陆游在表、启中每每始述“元祐家风”,自有其时代背景。盖自崇宁初年徽宗与蔡京三立“元祐党籍碑”,御书刻石于端礼门(文武百官常参必经之门),继而又令天下监司长吏厅各立其碑以来,此举已招致舆论相当之不满。朝堂之上士大夫的谏止之声尚且不论,甚至一般百姓对立碑之事也颇不以为然。《宋史·司马光传》载:“长安石工安民当镌字,辞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马相公者,海内称其正直,今谓之奸邪,民不忍刻也。’官府怒,欲加罪,泣曰:‘被役不敢辞,乞免镌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于后世。’闻者愧之。”则当时公道未泯,人心醇厚,至今犹可想见。所以迫于舆论,徽宗不得不放宽党禁,崇宁四年(1105)借名九鼎铸成之庆,诏赦“奸党”,翌年又借名星变,诏毁京师及各地已立之碑。 “元祐党人碑”不仅没有使“奸党”声名狼藉,反而提高了他们的声誉。这和文莹《续湘山野录》所记载的范仲淹“三黜三光”的著名故事一样,都是宋代“从道不从君”的士人精神及其群体自觉的体现。 下至于南宋高宗建炎、绍兴之世,朝廷为了笼络人心,团结御金,新政已改为褒赠元祐党人,且对党人之子弟据以“推恩”。高宗绍兴元年(1131)诏曰:“追复元祐臣僚官职,俄又录用其子孙”, 这正是陆游“偶以元祐之党家,获与绍兴之朝士”的历史背景。但陆氏每喜述其“元祐家风”的内在心理,绝不止于“陈乞推恩”而已,因为在他心中,“元祐党家”已成为一种政治品格的象征了。宋代之党争,其翻覆无常,诚有如苏东坡所谓“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八声甘州·寄参寥子》)者,且各党之间纷争互谤,错综复杂,即以“元祐”旧党而言,其中又有洛党、蜀党与朔党之别,其间得失利弊,自有史家之论。但如果撇开其为争而争的意气之见不论,则宋代党争未尝不是天水一朝士人群体与个体意识空前高涨的一种反映。党争之中,自不乏谋权射利,谗佞奸邪之辈,但守死善道,慷慨正直者,亦自代有其人。陆游祖父陆佃正是一位立身不苟,不肯阿比攀附的正直之士。《宋史》本传记载他曾“受经于王安石”,又尝与安石论新法推行之弊,后“安石以佃不附己,专付之经术,不复咨以政。安石子雱用事,好进者坌集其门,至崇以师礼,佃待之如常”。而当元祐初年罢废新法之时,“去安石之党,士多讳变所从。安石卒,佃率诸生供佛,哭而祭之,识者嘉其无向背”。 可见,陆佃之列名元祐党籍,正是因为其“尤恶奔竞”(《宋史》本传),且不“讳变所从”的政治品格。陆游心中的“元祐家风”正应从这一点上来理解。而彼时“元祐党家”之“种”,除陆游外,亦仍有尚在者。自崇宁五年徽宗诏命毁碑以后,“元祐党人碑”几已无存,但南宋又有党人子孙将其重新摹刻者,以表彰先祖名节,借伸“诎于一时,而信于万世”之义。 这仍然是士风犹盛的体现,和陆游“始述家风”、“先陈世德”的心理乃是相通的。
陈寅恪的“元祐党家”情结同样也并不止于对政治迫害的耿耿于怀,而出于认同和表彰先祖政治品格的一贯心理。且其重点不在政见的分歧,而在气节的敦守。世运之转移,恒以人心之厚薄与士气之升降为判,此一重心事,陈氏早在1945年《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一文中已和盘托出,而不待1958年“暗吞”其“伤春”之泪矣。《书后》云:
忆洪宪称帝之日,余适旅居旧都,其时颂美袁氏功德者,极丑怪之奇观。深感廉耻 道尽,至为痛心。至如国体之为君主抑或民主,则尚为其次者。……自戊戌政变后十余年,而中国始开国会,其纷乱妄谬,为天下指笑,新会所尝目睹,亦助当政者发令而解散之矣。自新会殁,又十余年,中日战起。九县三精,飚回雾塞,而所谓民主政治之论,复甚嚣尘上。余少喜临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盖验以人心之厚薄,民生之荣悴,则知五十年来,如车轮之逆转,似有合于所谓退化论之说者。是以论学论治,迥异时流,而迫于事势,噤不得发。因读此传,略书数语,付稚女美延藏之。美延当知乃翁此时悲往事,思来者,其忧伤苦痛,不仅如陆务观所云,以元祐党家话贞元朝士之感已也。
这段话真是写得无限感伤。陈氏蒿目时艰,心境渐趋于悲观保守,而使他最为痛心者,莫过于人心之厚薄与士气之升降。文末“悲往事,思来者,其忧伤苦痛,不仅如陆务观所云,以元祐党家话贞元朝士之感已也”一语(参前注),所谓“不仅”云者,即所“忧伤苦痛”,不在其数已无多,而在其气脉已尽。事实上,陈氏曾经“接其丰采,聆其言论”的“父执姻亲”之辈,正代表了士在中国史上的最后阶段。 《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引陈三立撰《巡抚先府君行状》云:“府君独知时变所当为而已,不复较孰为新旧,尤无所谓新党旧党之见”,且谓陈宝箴对当时“言洋务负海内重谤”的郭嵩焘“独推为孤忠闳识,殆无其比”, 这和陆游祖父陆佃在北宋党争中的立身出处乃是颇为相近的。陈三立所身历之时局世变,较其父而言,则尤为诡奇翻覆,但他在出处辞受之际亦能绍述其“元祐家风”。湖南新政时期,陈氏曾因谕旨引见而辞不赴诏,遂讲“抗旨之学”,谓:“中国人变法,当自抗旨始”。 这虽然和他接受西学新知有关,但也未尝不是“士志于道”的传统精神的自然流露。《陈三立传略》之撰者吴宗慈曾谓陈氏“在清末季,韬晦不出,与辛亥革命后之作遗民,其志趣节操,乃一贯而行者。……盖胸襟落落,自有独往独来之精神,寓于其间也”, 这是很能得其神髓的。至于陈寅恪称为“世丈”、“世交”的康有为和梁启超,虽然其思想政见与义宁父子颇有不同,但无疑都是陈氏理想之“元祐党家”中的代表人物。所以陈宝箴虽不喜康有为公羊春秋之学,却能深赏其“可用之才,敢言之气”,且谓:“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陈氏戊戌间上折请毁《孔子改制考》一书,正是保全康氏之意。 而梁启超一生志在改良,其思想与乃师又自不同。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曾以“旧是龙髯六品臣,后跻马厂元勋列”两句对梁氏有所訾议,而梁亦不以为忤。凡此都是所谓“君子和而不同”之义,且并不妨碍陈氏在经历更深之世变后,对梁启超“本董生国身通一之旨,慕伊尹天民先觉之任”,势不得与近世腐恶之政治绝缘的苦心孤诣,有了了解的同情。 而所谓“元祐党家”,正是由这样一些立身谨严,品格卓异,以天下为己任,既有个体之自觉,又有群体之自觉的“士”所组成的。所谓“平泉树石”,其具体内容亦不外乎是。
陈寅恪1945年已不胜其“悲往思来”之感,至1958年“暗吞”其“伤春”之泪时,“元祐党家”更已成为一种不名誉的身份了 ,则陈氏之“忧伤苦痛”,又当何如呢?现代的“元祐党家”已没有朝廷对之“褒赠推恩”,更没有长安石工为之一鸣不平了。比之于“偶以元祐之党家,获与绍兴之朝士”的陆游而言,陈寅恪此时尚不忘追述家风,其心为益苦,其事为尤难。虽然其时代背景颇为不同,但陆、陈二氏之不忘家风,以及南宋党人子孙重刻党人碑之与陈寅恪郑重珍藏《元祐党籍碑》拓本 ,若就其基本心理而言,仍可谓古今冥会,千载同符。从宋代的元祐党人到近代的戊戌党人,其间延续的正是中国史上最可宝贵的士人精神。戊戌维新虽因政变而告失败,而且发生了革职与杀戮的悲剧,但这是“元祐党人”坚守气节理想而愿为牺牲,比之于其子孙放弃气节理想而甘作傀儡,则六十年前之“天荒地变心虽折”,“若比”今日“伤春”之泪而言,正自“意未多”矣。
(三)释“未肯明流”:“义不受辱”的晚年心境
陈寅恪1945年的“噤不得发”还可藉《梁启超传》,以略抒其“党家朝士”之感。而他1958年“未肯明流且暗吞”的“伤春”之泪,就绝非六十年前“举国犹狂欲语谁”(《自励二首》)的梁启超所能想象于万一的了。“未肯”二字不仅是全诗的关键,也是我们通解陈氏晚年心境的关键。关于李商隐对甘露之变的反应,《邵氏闻见后录》曾保存了一条记载:“李义山《樊南四六集》载《为郑州天水公言甘露事表》云:‘宰臣王涯等,或久服显荣,或超蒙委任,徒思改作,未可与权。敷奏之时,已彰虚伪,伏藏之际,又涉震惊’云云。当北司愤怒不平,至诬杀宰相,势犹未已,文宗但为涯等流涕而不敢辩。义山之《表》谓‘徒思改作,未可与权’,独明其无反状,亦难矣。” 所以揆诸当时的形势,在古典之中,李氏的悲慨应是“玉谿满贮伤春泪,未敢明流且暗吞”,其意甚为明显。而陈寅恪变“未敢”为“未肯”,这正是他“融会异同,混合古今”的一贯手法,其中乃隐藏了陈氏最为幽微曲折的晚年心境。
从亭林诗的“韵目代字”到寒柳诗的“虚经腐史” ,这其中所深隐的乃是“遗民”从政治到文化的意义演变。陈寅恪晚年的幽微曲折主要是由文化上的人格自尊与时代环境的天壤悬隔造成的。他已不面临前代遗民那种“袍帽在左,白刃在右”的生死抉择,甚至方中履所谓“讳忌而不敢语,语焉而不敢详” ,在陈氏身上也已完全不再适用。他的“伤春之泪”之所以“未肯明流”的缘故,乃在于“明流”匪特无益,更适足取辱而已。对于一般流俗之见,陈氏自可以“留命任教加白眼”,“任他嗤笑任他嗔” ,而那些曾被他许为“并世相知”的人,现在也多已无法理解其“伤春”之泪了。陈氏1955年致蒋天枢函有谓:“弟往年挽王观堂先生七律有句云:‘吾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岂知果为今日谶耶!” 他当年所体会的王国维自沉时的心境,现在竟也变成了他的心境,言中乃是极为沉痛的。而所谓“晚岁为诗欠砍头”,其实同样也只能用王国维遗书的“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来互训,始能得其确解,陈寅恪所要说的正是一个“辱”字,所以“未肯”乃是陈氏“义不受辱”的一种明白表示。这种心境和情绪,甚至可以从他1959年在东南区一号楼阳台上留影的表情中得到印证。不仅《再生缘》的“不愿付刊经俗眼”是陈氏借端生之酒杯,浇自家之块垒,以释放其心中“骄傲自尊之观念” ;《柳如是别传》里陈氏以最复杂艰深的考证,通解钱柳因缘诗中天下后世而唯有他一人独得的隐秘,也正是此种情绪的宣泄 。因为惟其如是,才能使他在现实世界中孤独苦闷的心灵感到共鸣和满足。陈寅恪晚年的绝世孤高之慨,饮酣八极之哀,孤自暗吞,末由共喻,不禁使人联想到钱钟书和他的《管锥编》。事实上,《管锥编》中除去“触目皆是”的“感慨世变之语”以外 ,亦不乏钱氏“偶一流露”的“自抒己怀之辞”。如其论司马迁之受腐刑云:“盖谓宫刑变化气质,使人懦巽。征之迁《史》,岂其然乎?” 这与陈寅恪“伤春”诗句的着眼点虽不同,然要亦为藉古典以寄寓其“义有不受”的一种表示,他要说的其实是“征之钱《编》,岂其然乎?”因说陈诗既竟,附略及之,抑或可为世之以钱诋陈论者下一针砭乎?
结 语
陈寅恪晚年在史著中追寻的一直是“亲切有味”,因为现实世界中,“‘亲切’一词已是完全失去意义的语言了” ,他为自己建构了一个“思想、情感、价值、意欲等交织而成的古典精神世界”。“并世相知”既不可得,则陈氏一方面在史著中“抗志希古,尚友其人” ,一方面还可以期诸“异世相知”,即所谓“神州之外,更有九州,今世之后,更有来世”者 。“伤春”诗句写于1958年春,这年秋天,余英时在哈佛读到辗转流传至海外的油印本《论再生缘》,情不自禁地写下了后来曾被陈氏许为“作者知我”的《〈论再生缘〉书后》一文。1982年他又拈出“伤春”一联以概括陈氏的晚年心境,虽未及释证,要亦足当“作者知我”之意。且2007年余氏又写有《“反右”五十年感赋四绝句》,最后“人亡家破无穷恨,莫叩重阍更乞怜”一句适与“伤春”一联遥相呼应。所不同者,陈诗兼有“诗家之史”与“史家之诗”的双重色彩,前者指陈氏身历世变而发为歌哭的深慨奇哀,后者则是他贯通古今以铸入辞章的烛察先见。余诗则已褪却了“诗家之史”的沉痛色彩,保留了“史家之诗”的眼光与识见。然则陈、余二先生的异“世”相知,亦足以发我辈想慕之幽情矣。
〖作者简介〗熊烨,男,1984年生,湖南衡阳人。武汉大学法学学士,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民国词学与近现代古典诗歌。
—————————
注释:
余英时:《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版,第71页。按:余文引用原诗时将“未肯”误为“不肯”。
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下卷),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软精装本),第717页。
钱钟书:《故国》(1943年),收《槐聚诗存》,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89页。
陈寅恪:《读哀江南赋》,收《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34页。
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66页。
陈寅恪:《陈寅恪集·诗集》,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30页。
黄萱:《怀念陈寅恪教授》,收《追忆陈寅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
王应奎《柳南续笔》记严熊转述牧斋语,转引自《清诗纪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61页。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55页。
按:清华本《陈寅恪诗集》(147页)此处自注引录李诗作“金舆不返倾城色,下苑犹翻太液波”,而《曲江》一诗并无此异文,当系陈氏误记。三联本《诗集》(172页)当经编者改为李诗原句。然而正因为陈氏误记,他才会据此以为云起轩词“闻说太液波翻”即用李句,胡文辉《笺释》(914页)谓不知陈氏何据,当是一时失检清华本之故。又:《笺释》2013年增订本第1183页于文词出典有增补,可参看。
参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下卷),第848-850页。
胡文辉已指出此点,谓:“陈氏似即据冯浩的释解。”见《笺释》,第914页注①。
冯浩:《玉谿生诗集笺注》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46页。
此种方法亦自有其限制与缺陷,常有蹈空臆想之失,冯浩造为“分波”之说,即受到张尔田、高步瀛等人的批评,参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增订重排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53页。
以上参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下卷),第847-850页。
陈氏此一兴趣由来已久,如其1930年代致傅斯年函即曾有云:“赵斐云兄(按:赵万里)……所编晋南北朝墓志中隋宫人墓志一卷,披阅之,殊令人发思古之幽情。”见《陈寅恪集·书信集》,三联书店2009年第二版,第45页。
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下卷),第841页。
余英时:《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第71页。
吴宓:《吴宓日记续编》第五册,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63页。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第1074页。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09、311、312、317页。
陈氏分析顺、宪两朝史事时曾谓:“夫顺宪二宗帝王父子且为其(按:谓阉人)牺牲品及傀儡子,何况朝臣若王伾王叔文韦执谊刘禹锡柳宗元之徒乎?”其议论与李氏在诗中对文宗朝局的悲慨正复相近。见《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88页。
参张采田:《玉谿生年谱会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8页;《李商隐年表》,《李商隐诗歌集解》附录四,第2334页。
刘昫 等:《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462、4464页。
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文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10页。
参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下卷),第713-717页。胡氏以为此诗为有感于“梁思成批判父亲”而作,但陈氏此时是否确知梁思成有批判父亲的言论,尚有疑问。仅就“非吾子孙”的自注而言,若谓此诗是有感于“梁思成改易父志”而作,则较为稳妥。关于梁思成批判父亲一事在当时的流传,《笺释》2013年增订本第928页注②曾增补一则材料,可以参看。
陈寅恪:《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65页。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19页。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204页。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第82页。
按:此处陈氏误记,当为“两汉风俗”条。殆因“正始”条有“亡国、亡天下”之辨,陈氏牵合致误耶?可参余英时:《史学与传统》,时报文化公司1982年版,第296、297页。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第48-51页。
此陈氏《书杜少陵哀王孙诗后》(1953年4月)论杜诗之语,见《金明馆丛稿二编》,第64页。
此借用余英时先生《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一文中语,见《中国知识阶层史论(古代篇)》,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206、231页。
《陆放翁全集》(上),中国书店1986年影印世界书局1936年版,第3、50、51、57页。
陈寅恪:《寒柳堂集》,第150页。按:“元祐党家惭陆子”一句,据陈氏口述,蒋天枢笔录之自注亦云:“《渭南集·书启》有‘以元祐之党家,话贞元之朝士’。”然陆集中并无此语,吴宓、胡文辉亦未检获,殆陈氏牵合误记。“贞元朝士”本为熟典,出自刘禹锡《听旧宫中乐人穆氏唱歌》诗中“休唱贞元供奉曲,当时朝士已无多”一语,乃谪迁回朝,感念今昔之意。此典于陆游,亦可谓适切,且陆集中《谢致仕表》亦有“思正(按:即‘贞’,避宋仁宗讳改)元之朝士”一语,见《陆放翁全集》(上),第5页,所以陈氏误记,亦自有由。参胡文辉《笺释》,第71页;蒋寅:《“贞元醉汉”和“贞元朝士之感”补说》,收《金陵生小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元祐党人中多有流放岭南者,则陈氏此时所感或较往岁为尤深也。参陈乐素:《流放岭南的元祐党人》,收《求是集》(第二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参余英时:《漂流:古今中外知识人的命运》,《会友集》,明报出版社2008年版,第239、240页。
以上参陈乐素:《桂林石刻〈元祐党籍〉》,收《求是集》(第二集);任崇岳:《论“元祐党人案”》,《中州学刊》1992年第1期。
脱脱 等:《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917、10918页。
转引自陈乐素:《桂林石刻〈元祐党籍〉》。
参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新版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陈寅恪:《寒柳堂集》,第177、178页。
马卫中、董俊珏:《陈三立年谱》,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91页。
转引自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5页。
马卫中、董俊珏:《陈三立年谱》,第227、228页。
陈寅恪:《寒柳堂集》,第148页。
参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下卷),第714页注②。
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上卷),第70页注②。
邵博:《邵氏闻见后录》,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7页。
关于“韵目代字”究出谁手,参潘重规:《亭林诗考索》,东大图书公司1992年版,第3、90-105页;饶宗颐:《论顾亭林诗》,收《文辙:文学史论集》,学生书局1991年版,第706页。“虚经腐史”,参胡文辉《笺释》,第385页。
转引自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允晨文化公司1986年版,第9、113页。
陈寅恪:《陈寅恪集·诗集》,第137、149页。
陈寅恪:《陈寅恪集·书信集》,第275页。
陈寅恪:《寒柳堂集》,第58页。
陈氏谓:“数百年之后,大九州之间,真能通解其旨意者,更复有几人哉?更复有几人哉?”见《柳如是别传》,第563、564页。
余英时:《我所认识的钱钟书先生》,《情怀中国:余英时自选集》,天地图书公司2010年版,第154页。
钱钟书:《管锥编》第三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39、940页。
余英时:《未尽的才情:从〈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联经2007年版,第51页。
汪中语,见《与刘端临书》,《述学·别录》,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19页。
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8页。 |